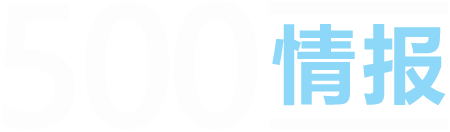彼得·德魯克逝世十周年 | 彼得·德魯克為我們指引的路
一直以來,,人們可以依靠彼得·德魯克為自己提供一種觀察事物的新方法,。畢竟,他是第一位認識到管理是一門值得深入和規(guī)范研究的學(xué)科的人,。遠在他人之前(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初),,他就預(yù)測到了計算機技術(shù)總有一天將如何徹底改變商業(yè)。1961 年,,他前瞻性地呼吁人們關(guān)注日本即將崛起成為工業(yè)大國,,而在二十年后,他又警告日本將面臨經(jīng)濟停滯,。至于“私有化”,、“知識工人”和“目標管理”等概念的提出,我們也可以都歸功于他,。
即使是在遲暮之年,,德魯克仍然充滿了眾人缺乏的洞見,并且對自己的信念堅持不渝,。他興趣甚廣,,從經(jīng)濟學(xué)、心理學(xué),、哲學(xué),、歌劇到日本藝術(shù),無不涉獵,,也曾經(jīng)為成百上千家大公司,、政府部門、小企業(yè),、教會組織,、大學(xué)、醫(yī)院,、藝術(shù)機構(gòu)和慈善組織提供咨詢,。甚至直到德魯克逝世前一年,這位管理學(xué)大師仍繼續(xù)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萊蒙特研究生院(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)的管理學(xué)院開講座,各行各業(yè)的領(lǐng)袖人物不斷前來加利福尼亞朝拜,,向他討教,。
在2004年距離這位教授的生日還有兩天的時候,《財富》自由編輯布倫特·施倫德(Brent Schlender)曾受邀,,到德魯克位于克萊蒙特的家里訪談,。于是,有了以下這段德魯克晚年少有的采訪:
《財富》:信息技術(shù)對商業(yè)的最重要影響是什么,?
德魯克:信息技術(shù)迫使你更有邏輯性地組織流程,。電腦只能處理答案為“是或否”的事情。它處理不了“可能”的事情,。因此,,重要的不是計算機化,而是你的流程要遵守的律令,。在你將流程計算機化之前,,你必須思考,否則計算機就會罷工,。
這種強制的律令會帶來一些不利之處,,因為它通常迫使人們處理事情時過分地簡化。此外,,形成商業(yè)決策的過程并不總是很有系統(tǒng)性的,,因而并不總是可以通過計算機來完成。你必須從決策者的想法中抽出各種假設(shè),,明白無誤地將它們與檢查這些想法的方法一起輸入到程序中,,只有這樣計算機才能幫你管理決策。老一代的經(jīng)理人發(fā)現(xiàn),,要搞得這樣明白無誤令他們苦惱,,因為他們就是不想這樣。此外,,我們都知道,,很多決策就像尿憋不住一樣,是老板被迫做出的,。
《財富》:既然企業(yè)如何計劃和運營方面發(fā)生了這些系統(tǒng)性變化,,你是否認為首席執(zhí)行官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變?
德魯克:在每次經(jīng)濟繁榮的時候,,都出現(xiàn)對首席執(zhí)行官的英雄崇拜傾向,。聰明的首席執(zhí)行官有條不紊地組建自己的管理團隊。但那些人們經(jīng)常提到的明星首席執(zhí)行官當(dāng)中,,有很多不知道團隊為何物,。而且,首席執(zhí)行官薪酬的膨脹,,已經(jīng)給管理團隊這種概念帶來很實在的破壞,。我在克萊蒙特研究生院講授的高管課程中,學(xué)生大都是很大的公司的主要部門的總經(jīng)理,,他們的報酬很高,。但公平地說,對于他們那些公司的首席執(zhí)行官當(dāng)中很多人的報酬過高,,他們是鄙視的,。J.P. 摩根有一次說過,公司最高管理者應(yīng)只拿普通工人 20 倍的薪水,。今天則更有可能是 400 倍,。我說的不是車間里的人們的辛酸感覺。他們已經(jīng)確信老板就是竊賊,。我說的是中層管理人員,,他們的希望令人難以置信地破滅了。因此,,目前的首席執(zhí)行官危機是一場嚴重的災(zāi)難,。讓我再次引用一句 J.P. 摩根的話,他說過:“首席執(zhí)行官只不過是雇來的人手”,。如今的首席執(zhí)行官忘了的正是這一點,。
《財富》:對知識工人的生產(chǎn)率,我們能怎樣衡量和提高呢,?
德魯克:還沒有人真正考察過從事科研的白領(lǐng)工作的生產(chǎn)率,。但每當(dāng)我們考察的時候,奇怪的是都毫無結(jié)果,。你知道,,我最近以來的研究工作涉及的是大學(xué)、醫(yī)院和教會,,它們是最大的知識工人雇主當(dāng)中的三種,,其生產(chǎn)率是令人沮喪的。某種程度上這是由于,,根據(jù)定義,,知識工作是高度專業(yè)化的,這意味著知識工人的利用程度通常是很低的,。
知識工人缺乏效率,,某種程度上是以下這種 19 世紀的信念的遺留結(jié)果:現(xiàn)代的公司試圖自己做公司的所有事情。現(xiàn)在,,謝天謝地,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外包,。但我要說的是,我們確實還不知道怎樣做好外包,。大多數(shù)人是用削減成本的觀點看待外包的,,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。外包所起的作用,,是大大提高那些為你工作的人員的質(zhì)量,。我認為,對于那些沒有可能進入管理高層的人的工作,,你都應(yīng)當(dāng)把它們外包出去,。當(dāng)你把工作外包給一名全面質(zhì)量控制專家,他就是在一年 48 個星期為你和其他客戶而忙,,他把這些工作視為挑戰(zhàn),。而如果公司雇傭了一名全面質(zhì)量控制人員,那么他一年只忙六個星期,,其余時間則在寫備忘錄和找事做,。所以當(dāng)你外包時,你的成本實際上反而是在增加,,但你得到了更好的效果,。
《財富》:很多高技術(shù)公司首席執(zhí)行官對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感到擔(dān)憂,尤其是對學(xué)技術(shù)的人越來越少這種現(xiàn)實感到不安,。你擔(dān)心嗎,?
德魯克:這種情況完全屬實。但他們忘了兩點,。我們是唯一一個擁有重要的再教育體系的國家,,任何其他地方都沒有。而且我們是唯一一個年青人可以很容易從一個領(lǐng)域跳到另一個領(lǐng)域工作的國家,。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,。如果你是會計,你就得是會計,。這在歐洲同樣是不可能的,。但在這里,這樣做很容易,。
因此,,與歐洲不同,在美國,,我們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在于雇員的自我組織性,。我意識到這一點,是因為當(dāng)我的歐洲朋友移居到這個國家時,,對于要面對的這種期待不知所措,。讓我們看一看這里很多人的職業(yè)生涯,。通用電氣首席執(zhí)行官伊梅爾特曾做過五六種不同類型的工作──銷售,設(shè)計,,為不同的產(chǎn)品部門工作,。相比之下,西門子的首席執(zhí)行官任此職位前從未在德國之外擔(dān)任過任何職務(wù),。
《財富》:你說美國經(jīng)濟如今受到了很深的錯誤認識的傷害。你能舉些例子來說明嗎,?
德魯克:美國經(jīng)濟的結(jié)構(gòu)與大家所想的有很大的不同,。好像沒有人意識到我們引入的工作崗位是輸出的兩到三倍。我指的是到美國來的外國公司創(chuàng)造的崗位,。最明顯的是外國汽車公司,,單是西門子公司在美國就有 6 萬名雇員。我們在輸出低技能,、低報酬的工作崗位,,但同時也在引入高技能、高報酬的崗位,。
《財富》:美國勞動力成本更高,、制造業(yè)進一步移往國外會危害到我們的貿(mào)易平衡。難道這種說法不對嗎,?
德魯克:工資成本如今只對很少幾個產(chǎn)業(yè)而言是最重要的因素,,即少數(shù)幾個勞動力成本占產(chǎn)品總成本 20% 以上的產(chǎn)業(yè),例如紡織業(yè),。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產(chǎn)品的成本中有多大比重可以歸為勞動力成本,,但這種比重很小,而且還在縮小,。以汽車零部件為例,。由于我提供咨詢,我恰巧了解世界最大汽車零部件制造商當(dāng)中的一家的內(nèi)部成本結(jié)構(gòu),。他們告訴我,,與進口相比,在這個國家進行生產(chǎn)還是非常便宜的(或者說在沿美墨邊境一帶的邊境工廠中生產(chǎn)時可能是這樣),,因為盡管這些零件是勞動密集性的,,但設(shè)計和制造也具有很強的技術(shù)密集性。當(dāng)屬于這種情況時,,我們在這個國家進行生產(chǎn)仍然可以干得不錯,。所以說,那種認為勞動力成本是在美國之外進行生產(chǎn)的主要原因的觀念,,只 是對很小一部分產(chǎn)業(yè)來說才能證明是合理的,。
因此,,正在將工作崗位遷移出美國的那些產(chǎn)業(yè)屬于比較落后的產(chǎn)業(yè)。對于很多比較先進的產(chǎn)業(yè)而言,,美國仍然是世界上從事生產(chǎn)的最便宜的地方,。我這樣說,不是因為我們的工資和薪水很低,,不是這樣,。但是,我們給雇員的福利比歐洲低很多,,而且美國工人更具靈活性,。我在此說的不是你可以把會計人員調(diào)去從事工程工作,我說的是你可以把人從芝加哥調(diào)到洛杉磯去,。在德國,,你敢這樣做?他們不會的,。這是他們龐大而又有限制性的雇員福利制度的荒謬副作用之一:讓一個人在魯爾地區(qū)失業(yè),,比調(diào)他到斯圖加特做一份實 實在在的工作還要便宜。日本也存在同樣的情況,。
因此,,我所說的“不可見”成本正開始迅速變得比直接勞動力成本更重要。它們是:養(yǎng)老金成本,,福利和醫(yī)療成本,,尤其是某些還沒有人評估的成本,我把它稱為“報告”成本,,它們基本上都是與遵守國家法規(guī),、稅收、勞資關(guān)系方面的要求等有關(guān)的,。
《財富》:你怎么看關(guān)于“美國存在失業(yè)問題”這樣一種普遍印象,?
德魯克:似乎沒有人意識到美國勞動大軍占人口的比例最高,比例遠遠高于任何其他工業(yè)化國家,。在西方,,我們的長期失業(yè)率最低。我們確實存在的失業(yè)現(xiàn)象,, 大多數(shù)并不是長期的那種,,而是短期的,人們處在“找下一份工作的階段”,,這個階段至多不過幾個月,。對于受過高等教育并想進入勞動隊伍的人來說,我們提供的好工作最多,。不像大多數(shù)歐洲國家,,我們的大學(xué)生基本上沒有失業(yè),。他們可能暫時沒有得到想要的工作,而且他們可能第一年得不到年薪 7 萬美元的工作,,但他們得到了就業(yè),。最后,我們還要考慮到,,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,,我們把所有想工作的婦女都吸納進了勞動隊伍,而且沒有發(fā)生任何動蕩,。這是相當(dāng)了不起的,。
《財富》:讓我們談一談美國經(jīng)濟的生產(chǎn)率問題。衡量生產(chǎn)率的數(shù)字不斷地提高,,甚至在增長遲滯的時期也是如此,。
德魯克:我認為你不能相信我們看到的有關(guān)生產(chǎn)率提高的數(shù)字,。但毫無疑問,,在制造業(yè),我們看到在理論和體系方面發(fā)生了一些可以與 20 世紀 20 年代的產(chǎn)業(yè)革命相媲美的根本性變化,。這些變化的發(fā)生,,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將生產(chǎn)計算機化和自動化帶來的,而是通過生產(chǎn)的系統(tǒng)化,。在過去,,人們提高生產(chǎn)率的方法是專業(yè)化。今天,,我們設(shè)計制造流程并在某種程度上設(shè)計分配流程,,與其說是使它們最大化,不如說是使它們最優(yōu)化,。而且,,新的制造系統(tǒng)將彈性植入到系統(tǒng)之中,而按照我們目前衡量生產(chǎn)率的方法,,彈性可能實際上會導(dǎo)致直接生產(chǎn)率的某種損失,。
你瞧,那些數(shù)字衡量的是工作進行的時候的生產(chǎn)率,,但它們沒有衡量工作不能進行的時候的生產(chǎn)率損失,,如你為制造某種不同的東西而建立工廠時的損失。我懷疑,,生產(chǎn)率的提高實際上要比所有這些數(shù)字顯示的更大,,因為新的、更具彈性的制造流程切實地消除了設(shè)立工廠等設(shè)施的時間,,而在此時,,制造工作是不得不停止的,。在有些情況下,這種設(shè)立時間從三個小時減少為四分鐘,。這并不會在我們的生產(chǎn)率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中顯示出來,。這些數(shù)字也沒有涉及能夠改變生產(chǎn)的構(gòu)成所帶來的價值,因為它們專注于傳統(tǒng)大批量生產(chǎn)行業(yè)的凈產(chǎn)出,。在我們一些較新的行業(yè)中,,我們還不太明白如何衡量生產(chǎn)率。
《財富》:美國是否仍在為世界經(jīng)濟定調(diào)子,?
德魯克:美國的主宰地位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?,F(xiàn)在正在興起的是由集團組成的世界經(jīng)濟,這些集團以北美自由貿(mào)易區(qū),、歐盟和東盟等為代表,。在這種世界經(jīng)濟中,沒有中心,。印度正在很快變成一個強國?,F(xiàn)在,新德里的醫(yī)學(xué)院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,。班加羅爾理工學(xué)院的工科畢業(yè)生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畢業(yè)生一樣優(yōu)秀,。另外,印度有 1.5 億人以英語為主要語言,。所以說,,印度確實在變成一個知識中心。
相比之下,,中國的最大弱點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小得令人難以置信,。中國在超過 13 億的總?cè)丝谥兄挥?150 萬大學(xué)生。如果他們要達到美國的比例,,他們就要有 1,200 萬以上的大學(xué)生,。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訓(xùn)練有素,但人數(shù)太少了,。還有就是中國巨大的內(nèi)陸地區(qū)農(nóng)村人口過多,、不發(fā)達。確實,,這意味著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的巨大潛力,。但在中國,吸納農(nóng)村勞動者進入城市而又不引起動蕩,,這樣的可能性看來很值得懷疑,。你在印度就看不到 這個問題,因為他們在吸收農(nóng)村地區(qū)多余人口進入城市方面做的工作令人吃驚──在沒有發(fā)生任何動蕩的情況下,農(nóng)村人口從 90% 下降到了 54%,。
大家都說中國的增長率達到 8%,,而印度只有 3%,但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觀念,。我們實際上并不了解情況,。我認為與中國的進步相比,印度的進步令人印象深刻得多,。
《財富》:回顧你的生涯,,有什么事是你曾希望做但卻未能做到的?
德魯克:有,,這樣的事不少,。我本來可以寫很多比我寫過的更好的書。我最好的書本來應(yīng)該是一本名叫《管理無知》的書,,很遺憾我沒有寫,。
我不后悔拒絕亨利·盧斯的邀請,他當(dāng)時請我出任《時代》雜志的國際新聞主編,,后來又請我擔(dān)任《財富》的執(zhí)行主編,。我想堅持教書,我想寫我自己的東西,,而當(dāng)你為一份出版物工作時,,你是無法這樣做的,。
我曾設(shè)想過做另一份工作,,但也沒有變成事實,對此我也感到很高興,。在結(jié)束了貝寧頓學(xué)院(Bennington College)的任教之后,,我計劃到哥倫比亞大學(xué)與一位朋友一起工作,他正創(chuàng)辦一個美國研究系,。當(dāng)時任哥倫比亞大學(xué)校長的德懷特·艾森豪威爾否決了資助的計劃,。他是削減開支的老手。我的錄用已經(jīng)得到學(xué)?;鹗芡泄芾砣说呐鷾?,并已經(jīng)擬了合同,當(dāng)時就等著艾森豪威爾簽字了,。
就在被告知我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那一天,,我離開哥倫比亞大學(xué),在第 116 大街進了地鐵站,,這時候遇到了另一位老朋友,,他在紐約大學(xué)教書。他跟我說他正要去哥倫比亞大學(xué),找一些老師幫助他組織紐約大學(xué)管理學(xué)研究生院的教學(xué)人員,。我甚至還沒上地鐵,,就在合同上簽了字。這就是我當(dāng)時怎樣當(dāng)上管理學(xué)教授的,。所以回想起來,,對于哥倫比亞大學(xué)的那份工作當(dāng)時黃了,我現(xiàn)在極其高興,。
譯者:水刃
-
熱讀文章
-
熱門視頻